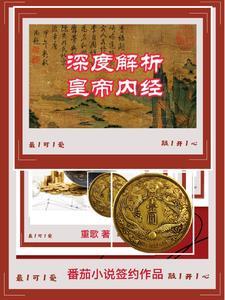华盟文章>听雨全文 > 第285章(第1页)
第285章(第1页)
“我明白了。”皇帝将自称换成了“我”。
沉默像是一把刀,很钝,割在手上或许没有伤口,可那些锈苔却攀着盘着之间,一点一点地蔓延上心头。
很久很久,金銮大殿中没人说话,只有一些很轻的,又很急促的呼吸声,风卷残云一样,好像在吸取着最后生命的价值。
“你应该很想知道,朕为何突然又愿意见你了。”皇帝的声音突然响起,听起来稍稍平静一些,只是带着一些倦意。
司若心头一动。
他当然会奇怪。
但他问不出这样的问题——雷霆雨露皆是君恩,纵使皇帝只是要单纯为褒奖他昨日劝退起义平民,然后将他流放千里,他也只得受着。
接着他便听到皇帝说:“昨天夜里,沈灼怀遭人刺杀。”
“什么?!”司若一惊,心中大乱。
“你别急。”眼看着司若眼睛都瞪大了,皇帝打断了他的话,“死的是那名刺客。”
闻言,司若瞬间松了下来。
沈灼怀没事,这就好。
但他是个聪明人,无需皇帝继续说,也随即明白了他的言下之意。
也怪不得外头的人全换了……沈灼怀虽不被皇帝所喜,但毕竟身处皇宫之中,明面儿上还是个皇嗣之后,却在宫廷守卫的眼皮子底下被刺杀……即使没成功,也摆明了这是有问题的。
一来,他们今日能刺杀沈灼怀,日后可能就能刺杀皇帝。
二来,若他们刺杀沈灼怀成功,那么皇帝这个位置甚至不必等他暴病身亡,就要被愤怒的百姓和不怀好意的群臣推得换个人坐。
今日他会宣召自己进宫,大抵也是意识到了这一切。
司若神色复杂。
“朕,思来想去,不想做个孤家寡人。”皇帝说。
“事已至此,沈灼怀身世如何,也与朕没什么太大关系了。”他望向司若,用一种很复杂的、带着一点奇异的羡慕的目光,“朕自登基以来,便没再能好好做过为人夫、为人父的本分,一切皆由这个‘责任’而承。”
司若有些不解地望向他。
这是一段有如临终遗言的话。
皇帝与他对视,眼中再也没有猜疑或是敌意:“我有我的安排了,你去见一见沈灼怀罢,年纪轻轻的,不要留下遗憾。”
“……臣明白。”司若轻轻叹息一声。
他行礼告退,离开宫殿时,外头已从来时的霞光漫天变成了昏暗的夜幕,侍女们一路小跑着,将沿路的油灯一盏一盏点燃,也将这昏昏夜色照亮。
司若缓步走着。
他得了旨意,终于能够去见沈灼怀,这分明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,可他想起皇帝最后的那些话,却觉得心里像是压着一块大石头。
司若转过身去,遥遥的望着宫殿。
殿门依旧开着。
灯火通明的偌大金殿中,景丰帝独坐在正中,什么也没做,就只是坐着。虽然身边总是跟随着很多人,可莫名的,司若却总觉得他像是被某种东西禁锢住了。
可怜。
这不是一个该用在皇帝身上的词。
可司若就是觉得他可怜。
第203章
更深露重。
凝结的水珠已经不会再化冰了,而是变成厚重的雾气,稠稠地挂在空中,在这种弥漫着暗色的夜里,仿佛一种有形的白色缎带。
沈灼怀坐在内室中,手边放着一把长剑,屋里点着一盏灯,将那长剑锐利光影反射成波折的碎片。
雾气似乎已经蔓延上这灯火附近了,映照出他虚虚的影子,长长地拖在地上,反映出沈灼怀扯咬着绷带,包裹受伤手心的修长身影。
他今早出去打听了些消息,得知京中一切安好,便没有妄动。
昨日杀人,来的那名御医大概是年纪太轻,行事战战兢兢的,加之又是深夜,沈灼怀手上旧伤的疤痕与新伤的伤口在血液中混在一起,难以辨认,手心难免留下了许多碎碴子,于是他只得自行处置。
这并不是个好活儿。
外头似乎又传来一些喧闹声,沈灼怀望了望窗户外的月光,已过亥时,大抵是护卫们准备交班了。
他听得身后传来一阵急急的脚步声。
“谁!”沈灼怀抄起长剑,划向身后——
剑光映照出一双带着一点惊讶的清冷眉眼。
一根发带被凌厉的剑锋划破,落下地来,随之而坠的是一头乌青长发,稍长的额发微微遮住一点微瞪的眼瞳。
风呜呜吹过。
这一幕,竟是像极了他们在乌川的相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