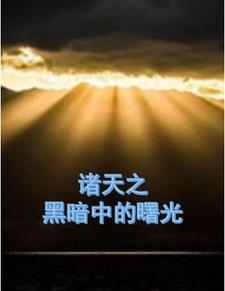华盟文章>怪物们的迷宫 > Ch 6 奶糖小姐(第2页)
Ch 6 奶糖小姐(第2页)
“尖角纯净蓝宝石,看女人哭了一夜的油灯里的灯油,母猫胡须…”
罗兰来回来去念叨,找了张长椅,往后仰把帽子盖在脸上。
耳朵就像兔耳一样,悄悄展开,从两边伸出帽子。
想想办法,罗兰,想个办法。
他听见有男士在聊怀表,工作,女人;听见女人在聊衣着、饰和唇妆:远在都的谁设计了什么内裙,又为了展示自己的纤足设计了什么短袜。
报童嘟囔着叫卖什么‘闲话报’,还算讲分寸;卖纸片火柴和牛奶的女士就有点惹人厌烦了。路过时,她们的声音尖锐的几乎快要划破罗兰的耳膜——他很快就猜到这种‘大吵大嚷’的售卖方式是一种故意的策略。
因为已经有人为了消停一会而花钱了。
好在‘老爷区’没有卖萝卜的,否则在那沉压压的轮碾和于胸腔共鸣的男声中,罗兰大概什么也听不见——能在这条窄街畅行的车,车轮都经过减音加工。
雅姆说这些老爷们的车厢甚至都抛光过。
可惜他看不见。
就在这时,一段很古怪的对话传了过来。
罗兰把头侧了侧,转动耳朵。
‘我是第一个,玛丽是第二个,伊莎是第三个,都记着了吗?’
‘你是第一个,我是第二个,玛丽是第三个?’
‘该死!你是第三个!’
‘那你是第几个?’
‘我是第一个!蠢货!一共三个名字,你都记不住吗?’
‘我就是记不住顺序…’
他听见一个女人在训斥,一个女人在嘟囔解释。
声音都很年轻。
‘好吧,现在换了。你是第二个,记着,拿到了就递给玛丽。’
‘拿到了就递给玛丽,递给玛丽,递给玛丽…’
‘你们不知道这家店新到货的珠宝价格有多高,我听说,有不少人等着要呢…’
裙摆路过罗兰,三个人的对话也清晰了起来。
这让他想起雅姆给他讲过的‘见闻’:或者说,某类身份不属于这里,却常年活动在有钱人世界的古老职业。
或许这是个机会。
罗兰想。
我不用等到夜里去砸珠宝店的窗子了。
打消心里的计划,重新冒出新的计划。他拄着手杖站起来,将帽子戴好,不远不近的坠着她们。
她们进了一家珠宝店。
人不少的珠宝店。
罗兰也跟了进去——顿时,他感觉自己就像钻进了座蜂巢一样,不仅拥挤,满鼻子还都是呛人的香味。
“快来,亲爱的!”
“我看看…”
“请把那颗鎏金耳坠递给我,谢谢。”
罗兰低着头,穿梭在人群里,用耳朵找那三个姑娘。他压低帽檐,踱步来到一个柜台前站好——只要不乱动,忙碌的售货员是很难看出人群里混进来一个几乎身无分文的睁眼瞎。
至少他穿得像那么回事。
“让我看看那支红宝石胸针,对,您说真是巧,我就缺个红色的。”
他听见那女人把自己声音刻意挤得又黏又甜(像雅姆上个新年给自己吃过的那块三角奶糖),等售货员递上胸针后,她又开始跟两个好友讨论起上面的设计和工艺,直到另一边有人呼唤走售货员。
罗兰听着她们小声嘀咕,将那枚胸针来回传阅;接着,靠近自己身边的位置有了几乎难以被察觉的动静。
很快,售货员又被她们叫回来了。
“让我看看那条项链吧。”
奶糖小姐好像完全不记得刚才胸针的事儿,颐指气使地吩咐售货员——这也让罗兰终于确认了她们的身份。
有钱人才不这么说话。
如果讽刺和傲慢能被下等人听出来,那还怎么显出他们使用着另一套语言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