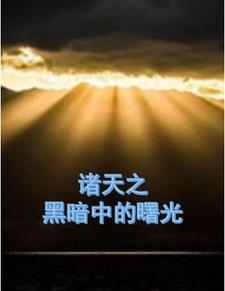华盟文章>临时恋人 > 第24章(第1页)
第24章(第1页)
谢槐夏:“对!不对!小姨你怎么可能不好!你最好!”
谢安青自嘲般笑了声,已经压得很低的肩膀继续下沉,然后直起身体说:“记得你说过的话。”
谢槐夏点头如捣蒜,惹得就住斜对门的张桂芬乐不可支,顿时更想自己那个远在千里之外的孙女。
谢安青看着她,心里对后年年底这个时间其实没有十足的把握,但人变老的速度永远不会因为她没把握就网开一面,那她就只能回头来逼自己——两年半,不行也得行。
那对陈礼,这个能帮他们把东西卖出去的人……
她还不能撕破脸。
可这也不代表她会继续无底线的退让,或者干脆把自己搭进去。
希望陈礼看得懂她昨晚的意思,及时止损,否则,她不确定自己还能和她和平相处多久。
就像那枚被扔进垃圾桶的创可贴。
她这人有时候可以非常不识好歹。
谢安青把车撑在树荫下,顺手捏了点鱼食。
二楼那扇窗依旧开着,陈礼疲懒地横趴在床上看昨天还开得正好,今天就几乎全部凋落的月季。花瓣层层叠叠堆在窗台上,晨光斜过去,把花瓣的轮廓描成窗台上的影子。
很有感觉的画面,陈礼一整晚辗转反侧的起床气都被打散了。她撑坐起来,勾起右侧掉落的墨绿色睡衣肩带,准备取相机拍几张。
余光透过窗户瞥见鱼池边的人影,陈礼步子顿了很长几秒,然后调转方向,侧身坐在飘窗上,单臂搭着窗棱,头靠上去,漫不经心地看着谢安青把落进鱼池里的花叶一片一片捞上来,之后拖来水管,把院里的花花草草全部洒了一遍。
今天是晴天,早晨八点的阳光不慌不忙落上去,陈礼在白天看到了深夜闪烁的星空。
谢安青只觉得再稀松平常不过,她身上覆了一层蒸腾上来的水汽,潮湿闷热,捂得人很不舒服,所以把水管盘好堆回到原来的位置后,她顺便弯腰在水槽前洗了洗脖子和脸,又凑过去喝了两口凉水,才顶着湿淋淋的水珠子往屋里走。
经过屋檐,头顶忽地传来一道女声:“谢书记。”
还是那副从容熟稔,游刃有余的,谢安青不喜欢的腔调。
看来她没打算懂她的意思。
谢安青映着水色的眸光有一瞬下沉,过后平静如常地抬头,水珠从她发根滚进耳朵,一些从脖颈滑入衣领。
陈礼侧身趴在窗棱上,浑身沐浴晨光,她被晨光打亮的眼睫在触到谢安青下巴的水珠时轻轻一闪,短得她自己都难以察觉。
谢安青就更看不见,她只是保持仰头的姿势,看见陈礼自然下垂在窗外的手里捏着一支月季。已经开败了,花蕊上剩孤零零一片花瓣,被陈礼在墙上轻轻一磕,旋转着飘落下来。
二楼到一楼的距离本来就不远,这会儿还一个垂着手,一个站直身,距离进一步被缩减,于是飘落的花瓣只能荡短短一截,还没来得及改变方向,就按照既定路线落在了谢安青肩膀上。
谢安青眼尾往下瞥。
陈礼晃着彻底秃了的花蕊说:“早上好。”
水从谢安青下巴滚落,同步着这一天的第一声蝉鸣。
还不尖锐,穿过葳蕤树叶,和水汽一起蒸腾着向上,让人燥,让人湿,更让人闷。
“早上好。”
片刻后,谢安青的声音从楼下传来。
她已经进了堂屋,陈礼在她的身影消失之前,看到她动了一下肩膀,花瓣便顺着衣服直直落在地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