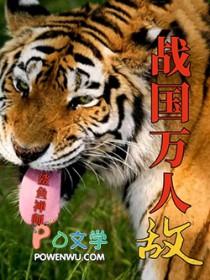华盟文章>旧日故事世代上演 恋恋不舍不弃 > 第19章(第1页)
第19章(第1页)
我冲你笑了笑,你朝我扔上来一颗糖。我捡起来装进口袋里。
那天晚上,我拿着证件,带了一点钱坐上了南下的火车,很多人往回赶,我却往外走。我那时并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,我坐在铺着白色餐布的窗户旁,希望火车能载我到无何有之乡,虚无才是我的归宿。
第三天早上,火车经过一段山坳,晨曦下朝阳虽然火红,但能直视我看了一会儿,从口袋里掏出那颗糖。
硬水果糖。
我听到一阵钟声,空寂广阔,像是从虚无之地传来。我在最近的车站下车,打听这里是否有寺庙。
这是另一段机缘。我顺利找到禅音寺,暗红的大门在台阶上。何处是归程,此处便是归程。
五年后,我开始给寺里的义工讲金刚经,讲了十年,香港霞光寺重建,我去当主持,继续讲经。
十年前,你来香港讲学,我在报纸上看到你讲逍遥游,疑惑你何时转而研究东方哲学。大概西方哲学找不到答案。
那天我讲楞严经。傍晚下课,霞光满天。我在霞光寺的樗树下打坐,遥想某年我与你在饭桌前,你同我讲,彷徨乎无为其侧,逍遥乎寝卧其下。
很快入定,立蚁背浮乎江湖,藏鲲鹏于袍袖,破二相,入等持次第。
一个月前霞光潜梦,你于霞光之间转身向我笑。这笑容我执多年,终于等到。于是出寺,坐船,坐车,步行来见你。人生如南柯一梦,你的梦要醒了。
我来见你,没有什么要讲。
我对你唯有一句我爱你,这多年前就已说过,再说仍是回声。跋山涉水来说这些,只是告诉你回声从何而来。
我爱你,这一念中有三十二亿百千念,念念成形,形皆有识,识念不可执持。这便是一千二百八十兆个的生滅,一千二百八十兆个平行空间,所有我才说我对你的爱在爱的那一刻就已经永恒,存在于每一个平行空间里。
我对你的爱,自那时起,就是无限空间里的永久沉默。
褚长亭讲完,静默片刻。颂经。
陈逍看到陈景同面容平静,虽然没有睁眼,但像刚笑过一样。
褚长亭颂完经便要离去。陈逍在他前方引路,下楼路过主卧窗下的花园,粉色的八月菊迎风飘摇,露水在阳光下晶莹剔透。
褚长亭看了少时,问陈逍自己能否摘一朵,陈逍拿剪刀减掉一朵递给他,“他从来没有结过婚,我是他的养子。”
褚长亭笑了一下,眼角皱纹慈祥,“你他的遗物时若有见到一个红布包着的佛像,可能行方便送到霞光寺来?”
陈逍点点头,送褚长亭出门。这僧人穿着布满尘土的僧衣,手持一朵八月菊走在明山小路上。若拍下,也应该是个很好的摄影作品。
陈逍目送他走远,回到主楼,佣人说陈景同已经断气。
陈逍操持完陈景同的葬礼,头七陈景同的遗物,真在书架暗盒里找到一个红布包着的玉质佛像,还有几封未寄出的信。信封上写着长亭和日期,每十年一封。
过完五七,陈逍出发去香港。
去之前搜索褚长亭,发现对方在霞光寺法号叫不悟,网络上有许多他讲经的视频,确定当天在明心山庄的就是同一人。
陈逍到霞光寺时是下午,他对这里并不陌生,因为每年冬天陈景同都要来一趟,在附近走一走。
寺里香客很少,五十一个台阶后入大门。陈逍在大殿里跟一个和尚说自己要见不悟法师,那和尚听后说:“不悟法师外出回来当天便坐化,昨天已葬塔。”
陈逍说:“我这里有一些他的旧物,交给谁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