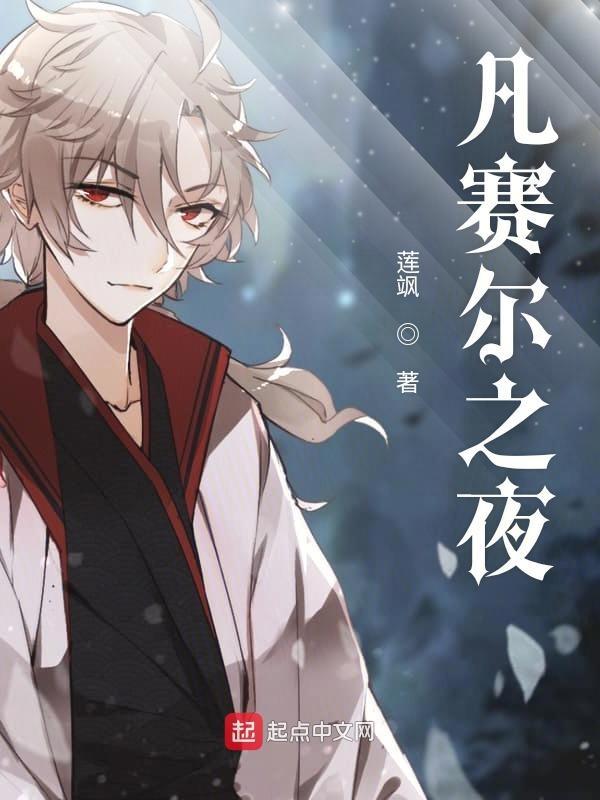华盟文章>高高的向日葵像什么 > 第79章(第1页)
第79章(第1页)
她永远记得初中的那个夏天,她被一群女孩堵在学校后面的树林,她们要扒她的衣服。世界末日的时刻,是那样一个男孩,从林荫的操场上走过来,肩上有阳光的穿透梧桐树影落下的斑驳,他救了她不容被打破的自尊心。
她的爱情,不是一场虚妄的不知所谓的迷恋,她是真的喜欢。然而,她不知道,她心心念念的这段往事,却是陈墨早就遗忘的故事。
杜依依在陈墨的人生中,永远是一个逗点,讨厌地粉红色的逗点,任何句子,都不会以逗点结束。一个逗点,注定是过客。
安乐想,如果这世界上真有无辜的人,就是杜依依了,可惜,好人往往没有好报。如果陈墨爱的是杜依依,应该是最简单的幸福。
然而,‘如果’这个假设性的前提,永远不成立的居多。安乐不愿为别人的感情哀悼,太假惺惺。她选择这样欺骗的方式步入杜依依的生活,就注定在未来,谎言被识破的时候,接受惩罚。
谎言之所以是谎言,总有被揭穿的一天,知道她和陈墨关系的,还有梁洛,那是个定时炸弹。在一切败露前,她要竭尽全力,拿到那块地。
老人说,说谎的人死后要下拔舌地狱,她不相信命运,更不相信这些神神鬼鬼的传说。
因为,她生活世界本来就是无边的沼泽,就是地狱。还能糟糕到哪里去?她很知足,她爱过,享受过片刻的温暖和甜蜜,就够了。
“我最讨厌别人骗我,不过你算例外,隐瞒算不算欺骗?哈哈,安乐,我们挺有缘的。”杜依依举杯,金色的香槟有小小的泡泡,碰到她手中的,清脆的响。
“是啊,难得。”
“我觉得你特别对我脾气,年纪差不多,连癖好都差不多,没事你常来找我玩呗,放假好无聊。”
“好。”
“那过年你来我家,我给你看我收藏的那组hellokitty,全是限量版!”
缘分,不是好的。安乐微微垂下睫毛,覆盖住晶莹的眼眸,她通过那个收银员的事情,便知道杜依依的性格。好,会对你好到极致,恨,也会不择手段。
努力
车里cd机放着齐秦的《夜夜夜夜》,安乐原本不知道重复的词语有什么意义,然而听着凄婉的乐调,蓦地就明白了。每一次重复都更加深沉,像跌入无边的黑暗。讨厌伤感的音乐,影响此刻的心情,她伸手,食指轻点,声音嘎然而止,逼仄的车厢顿时安静下来。
陈墨不说话,像他的名字般,而上升的车速暴露了他隐隐的怒意。
为什么生气,安乐很清楚,是因为自己擅作主张。可是一开始的计划便是如此,总要有人继续下去。她并不在意做事情需要善始善终,她一直是被生活戏耍的人,字典里从来都是见机行事,三十六计走为上。可她现在,居然挺胸而出担待了一把,换来的却是某人紧绷的脸。
车子很快开到公寓。陈墨进门首先就将趴在沙发上看电视的孟行丢出去,动作行云流水,迷迷糊糊的孟行连完整的“老大”还没来得及喊出一半,就被“砰”的关门声打断,鼻尖差点被甩上的门撞到。
发怒是弱者的行为,陈墨对自己说,可是,看似风清云淡的性子却一再被安乐打败。她和没事人一般,坐下来拨拉着茶几上的遥控器,无声的频道变换着,光影闪烁,照得她的脸若隐若现,昏暗的房间看不清表情。
“你难道不应该对我说些什么?”陈墨忍住想上前打她屁股的冲动。
安乐身子僵了一下,说什么?人的心思总是那么复杂,她此刻也不能弄明白自己究竟是怎么想的。就像一场战争,她本来是敢死队末尾的一员,随时打着溜走的主意,而最后,居然变成挺身而出顶炸药包的人,这不是很好笑的事情么?
空气在周围凝滞,安乐并不想解释,解释更多的时候是掩饰。她像只别扭的刺猬,敞开了肚子最柔软的地方,做了显而易见的事情,去表达她的心意,却笨拙的连‘啾啾’地讨好声也不会发出丝毫。
他们谈话的次数回想起来,屈指可数。他教给她的,都是防备和进攻的技能。此刻,最简单的交流却让两人像哑巴一样,相对无言。
终究是陈墨败下阵来,他一把拉过安乐,按在胸前。怀里瘦弱的身子微颤,他的手臂缠上了她单薄的不盈一握的腰。
他在他耳边低声说了句:“傻瓜。”简单的两个字,百转千回。
安乐觉得男人手臂上的丝丝热气,似乎透过层层衣服,熨烫着她的肌肤。
傻瓜。可不是吗?在爱里的人,不是傻子,就是疯子,他又聪明到哪里去。一错再错,溃不成军。
他打开灯,温暖的橘色倾洒在整个房间,她脸上的妆,经过一晚上,黑色的眼线和睫毛膏稍稍有点晕染,眼睛却更显的大而深邃。陈墨微微一笑,将她抱了起来。
“干吗?”安乐难得终于开口,伸手抵着他的胸膛。
陈墨也不回答,几步路走到浴室,用手肘按开灯,将她放坐在浴缸的边沿,安乐有点不知所措。鸳鸯浴?她脑袋闪过不纯洁的画面,脸上有点绯红。而陈墨却只是在洗漱台上俯身找着什么,再转身,拿出一管洗面膏,挤出一点在手心,放在水龙头下浸湿打出泡沫。
在安乐还很茫然时,温热的手掌覆上了她的脸,“闭上眼,小熊猫。”
他的指腹滑过额头,掠过颧骨,在眼睛周围画着凌乱的圈,笨拙。安乐的手抓住浴缸的白瓷,然而感觉不到凉,清淡的香从他的掌心蔓延开,像有朵芬芳的花瞬间盛开,她目不能视,触感就愈发敏锐。